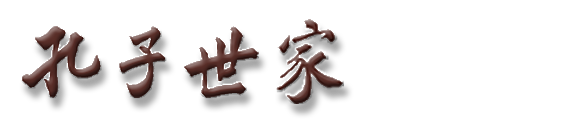自上世纪80年代大陆“韦伯热”兴起以来,围绕韦伯这位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家的研讨和争论似乎从未平息。其中最具争议、也最吸引国人关注的或许是马克斯·韦伯那著名的疑问:在传统中国的漫长历史里,这片土地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欧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韦伯断言,除若干物质与结构性因素外,“儒教”是阻碍资本主义的萌芽重要的原因:它倾向于维护、肯定现世而缺乏变革现世的动力,使得以传统主义为取向的中国文化难以萌发现代社会发展所必要的理性主义因素。
在中国,这个论断曾引发焦虑:既然儒家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只有抛弃儒家、引入韦伯所谓的新教精神,我们才能赶上现代世界理性化道路的末班车?它也招来质疑:先不谈儒家能不能算作“儒教”,韦伯在论述儒家思想中大量论证细节本就有违史实,况且,莫非儒家不能和新教一样自成一类现代化范畴么?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我们是否赞同韦伯,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并面临传统与现代种种冲突的中国来说,韦伯都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对话者:哪怕在细节上常有偏失,却很难再有一位学者像他那样既能精准地运用“理想类型”来把握特定社会系统所隐含的逻辑和问题,又能尊重理论分析和现实历史之间张力,尽可能广泛地进行历史的、比较的研究,以在东西交汇的视野下呈现不同文化系统的复杂性。
一直到今天,如何阅读马克斯·韦伯,或者说如何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斯·韦伯,激励儒家与韦伯的对话和相互阐发,思考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体系的得失,并探寻“传统”在现代新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日,北京大学文研院召开了“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试图呈现会上中外学者有关韦伯和儒家的讨论与见解。
一、韦伯眼中的儒家:太和平的,太入世的?
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儒家,“新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对比项:在那本堪称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带有理性计算特质的、追求和拥护经济利益的精神,认为正是新教伦理里禁欲主义、职业劳动等观念,带来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诸要中里最基础的理性行为要素。而当我们试图理解中国在韦伯现代历史图景中的方位时,便必须首先把握新教在西欧现代化和理性化中的重要动力作用,以此询问:到底新教和儒家有什么区别,让韦伯断言后者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叶翰(Hans Van Ess)教授首先指出,在韦伯的论述中,和平主义是儒家区别于新教的一个显著特点。韦伯认为,儒教主要是和平主义的,秉持儒家原则的政治文人主导了公共意见并形塑了民族气质:相比起追随具有超自然或超人色彩的卡里斯玛,他们更肯定传统对社会和政治原则稳固持久的指导意义;相比起追求领土扩张和经济竞争,他们更推崇仁厚的风气,良好的涵养和“君子”式的美德。作为两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治阶层,这些儒士从根本上是个和平主义者,以内部的政治安宁为取向。
与此相应,与长期分裂的、充满战乱与纷争的西欧历史不同,中国历史似乎总是维持着统一而稳固的帝国景象。但恰恰是这种和平主义取向和长期和平的历史减缓了变革和发展的动力——叶翰指出,韦伯并不否认战争为人的生命、财富、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创伤,但他同样强调战争的积极面向:欧洲国家之间为了资本或领土的长期战争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时常带来政治建制的变革,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儒家精神,以及支撑这一伦理的社会制度,都在各个层面上压制了具备变革潜力的种种竞争因素。
韦伯这一判断自然有其缺陷:由于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耶稣会士对儒家描述的影响,韦伯口中的儒教和平主义事实上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他忽视了儒士在实践中未必和平的一面,也忽视了中国历史中战乱和纷争的阶段。不过归根究底,“竞争与和平”的分歧只是新教与儒家更深刻分裂的体现——当韦伯强调儒家的和平主义性格时,他强调的是儒教对传统的维护,及其坚持适应现实世界、肯定现实世界的倾向。正如韦伯自己所说,“清教与儒家一个更根本的分歧在于对待世界的态度”。
那么,二者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有何不同?正如李强教授所说,在新教的世界观中,现世是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而人生在真正意义系于在彼岸世界得到灵魂救赎。由此,“彼岸”的超验价值和“此岸”的世俗世界始终存在某种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会在实践中构成一股转化的力量,引导人们去批判、变革现实;儒家所缺乏的,恰恰是“此岸”和“彼岸”两个世界之间的基本张力——就像费瑞实(Thomas Fröhlich)教授对韦伯有关儒家“彻底的现世乐观主义”的解释那样,儒家伦理要求对于现实世界一种近乎无条件的肯定和适应,它移除了世俗世界与个体超世俗目的之间那基础的、悲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彻底肯定性的世界观从根本上忽视了个体拒绝现世的伦理能力,因而成为变革社会现实的结构性阻力。
换言之,是倾向肯定还是否定现实,是否具有超验价值的引导,是否存在世俗世界与超验价值之间的紧张,划定了新教与儒家的根本分歧;而在韦伯的世界历史图景中,儒家所缺乏的这种“两个世界的张力结构”正是理性化与现代化的重要促因之一。
二、一种回应:儒教真的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吗?
通过否定儒家具有两个世界的张力结构,韦伯进一步论述了为何儒家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一方面,对现实的肯定态度使之难以将经济的理性主义发挥到最彻底的境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彼岸”超验价值的引导,商人对财富的追求在儒家语境内绝不包含新教伦理意义上的“召唤”或责任。
韦伯对儒家的论断在学界受到诸多争论和质疑。而在会上,田浩(Hoyt Tillman)教授重点介绍了学者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那颇具代表性的反驳。我们看到,如果说韦伯通过否定儒家“两个世界”的结构来否定了超验价值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指导,从而将中国人的商业活动化约为纯粹的营利活动,不认可其具有任何商业伦理或价值导向的话,余英时则力图梳理唐宋思想领域 “入世转向”以来禅宗、道教和儒家对待超验价值与现实社会的复杂态度,从而说明中国宗教、尤其是儒教确实存在“此岸”与“彼岸”两个世界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又确实带来了一股参与和改造社会的力量,并转化为明清商人的内在精神内核。
具体而言:
首先,因“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余英时试图论证中国宗教对国人勤俭的生活方式的塑造:诸如在慧能的引导下,新禅宗与传统佛教产生分歧,开始关注社会并提倡“不作不食”的劳动理念;而新道教不仅鼓励人们参与劳动,还试图在理论上中和“有为”和“无为”之间的矛盾;新儒家对“勤”的推崇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国人的勤俭信念。
随后余英时指出,宋以来无论是“天理”与“人欲”还是“理”与“气”等概念,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新儒家“两个世界”的意识。而儒家对世俗世界绝非仅仅是适应的态度——它同样试图依据“道”或“理”来积极参与并改造现世。新儒家一方面承续了新禅宗的修养工夫,一方面则在世俗伦理上有更进一步扩展——一个关键概念是“敬”,即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就如同新教教徒对自己的只有抱有某种“使命”、“天职”感一样,儒士也在实践中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而商人呢?随着新儒家伦理的扩展,宋代已经有了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儒家商人并非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只有营利欲,他们同样发展出了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并对自身事业抱有价值上的信念。
由此,儒家(以及禅宗、道教)都确实在积极意义上推动了商业精神和商业伦理。田浩指出,余英时眼中真正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阻碍的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即过高的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官僚系统压抑了商业的自由。
三、在多元因果和整体结构中看待儒家
事实上,韦伯从未断言唯有新教伦理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强调两者间“选择的亲和性”——毕竟,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没有哪一个或几个因素能占据决定性地位。而无论余英时的反驳是否有效,它至少显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单一地聚焦于儒家,是不能让我们真正把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方位的。然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复杂因果的纠缠关系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儒家在我们社会和生活中的作用?
会议学者达成的一点见解是,在肯定宗教对个体现实行动之作用的基础上,可以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宗教。换言之,无论是对待儒家还是新教,我们都可以试图从韦伯对伦理人格和生活样式的整体探究中看待他们的作用。正如王楠所说,韦伯之所以重视乃至推崇新教伦理,是因为新教所推动的生活方式正契合韦伯对现代人伦理人格和伦理关系的期望,即将对理想的追求置于日常伦理实践和生活内,使之转化为一种伦理品质,并在集体生活中通过伦理规范和相互鼓励形成现代的伦理关系。同样地,拘泥于儒家是不是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它对中国人伦理实践和主体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现代生活中的可能意义。
此外,王楠进一步提出了在整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看待宗教作用的想法:就像宗教形塑或引导个体社会行动之主观意义和意图那样,当我们将这个个体纳入有逻辑的行为体系或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去时,同样可以考虑这个组织结构“正当性”的基础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在这里显现的是韦伯支配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的关联:王楠认为,在讨论卡里斯玛支配类型转化的过程中,韦伯已经意识到必须将正当性作为社会组织支配类型的基础;而特定支配类型的存续,则要求该组织内发展出对支配之为正当的普遍信仰——换言之,宗教和神圣性的社会维度是支配社会学“正当性”讨论中不可或缺的面向,它们提供了“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政府/党派/团体”的基本理由,并带来共同体伦理结构和实践的根本动力。
总言之,在多元因果观念和整体社会分析的视角看待儒家与宗教,我们会看到:它是多重因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变量,也是整体系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维度,并与其它因素协同作用促成整体的变迁。 形塑了我们生活方式和伦理人格的宗教,同样也是我们对特定组织结构和支配类型正当性信念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