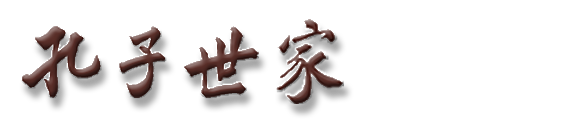编者按:“儒学不只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传统的话说,它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术思想……”台湾学者林聪舜近日出版了《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文简体版,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寻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又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还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本文节选自本书的第六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
“更化”以建立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
任何政权若想维持稳定的统治,除了依赖镇压性的力量外,尚须借助意识形态的说服,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在汉武帝以后的帝制中国,长期扮演意识形态说服工作,亦即扮演帝国意识形态角色的是儒学,而董仲舒在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在于他改造先秦儒学,使它更能适应帝国的需要,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统治秩序的核心思想,能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由于董仲舒的儒学是帝制中国首度出现的较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本章将以此为例,具体说明儒学如何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使儒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得到更确实的了解,也使儒学何以能在长达二千年的帝制中国,一直扮演正统教义(orthodoxy doctrine)的角色,而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得到更圆满的解释。
依照董仲舒自己的说法,他把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称之为“更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更化”的建议,谓:“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更化”的内容是董仲舒心目中的儒家伦理与儒家秩序,最后的发展则是在第三次《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下面一段引人瞩目的言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种透过仕宦之路的控制,打击“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外的思想,借以达到“统纪可一”“法度可明”的统治思想目的,是意识到思想文化所能发挥的力量,想运用政治权力把儒学抬举到独尊的地位。虽然西汉罢斥非儒者并非发自董仲舒,但是他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做出全新且整体的解释,亦即他能以重新塑造的儒学“更化”,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使儒学能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这就标志了儒学的新纪元。所以班固把汉代隆儒的成效归功于他,谓:“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此处应注意的是,本文虽认为董仲舒的儒学扮演着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并且认为他独尊儒术的主张具有思想统治的目的,但此一解释并不着重价值判断,亦即不具有贬义,而是把它视为历史事实来看待。本文乃是企图透过此一角度的研究,更深入发掘儒学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政治社会功能,以及儒学思想发展背后的权力关系。
尊儒与意识形态控制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主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简要有力地表达了董仲舒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用心。
透过意识形态控制,达到统纪、法度的齐一,并非始于儒家,而是法家首创的。《商君书》就反对人民信奉法令以外的知识;《韩非子》更重视思想统制的工作,认为国法的标准若与世俗的毁誉不同,将造成国法权威的陵替,“治强不可得也”,所以主张统一价值标准,排斥儒、侠、纵横、带剑之徒,希望达到以法的赏罚为唯一的价值规范。后来李斯《焚书议》主张焚书的理由,是害怕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思想,造成不同的价值标准,使国家的“法教”丧失独一无二的权威性,使国君的权势受到损害。这种主张与韩非完全一致,所以秦始皇的焚书之举,是法家理论的实现,一点也不偶然。
然而,秦帝国未意识到儒学除了具有“以文乱法”的腐蚀统治秩序的作用外,更具有稳定统治的功能,端看统治者如何运用。是以秦帝国统制思想的手段偏重镇压性,所以没有达到意识形态说服的目的,秦帝国的思想统制算是失败了。
董仲舒尊儒的方式是透过仕宦之路的引诱,“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办法配合当时的贤良、文学已由儒者包办,结果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可以看出“禄利之路”发挥了预期的功效。董仲舒尊儒的更具体方式是立学校之官,地方推动儒学教化,“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在武帝要求下,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上奏具体办法: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代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诞生了。
武帝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但他并非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关怀上,他相当依赖方士;在政策推动上,又相当依赖法家。例如在封禅这件事上,儒者就不能像方士一般满足他的需求。尽管如此,由于利禄之路的引导所形成的风气,不但儒家的教化逐渐普及,儒家经典也为全国上下所必读,上至帝王太后、下至公卿大臣无不读经,甚至平民读经以求进阶者亦蔚为风气。后来的宰相也都由熟读儒家经典者担任,“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经典是储藏价值观念的仓库,在儒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读物,甚至是生活教科书后,它在意识形态的说服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
思想统一的效果,照董仲舒自己的说法是“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确,透过政治力的介入,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全民的规范,经学义理成为政治社会活动的指南。例如在“大一统”的观念下,诸侯将相养士的风气为之一变,就如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这是认为士仅属于皇帝所有,是思想一统在政治一统上的反映。又如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这虽也是“缘饰以儒术”,但仍可以看出《尚书》《春秋》在决狱上的权威性。经学义理是决狱的指南,当然也是行动的指南。再如由儒学义理发展而成的三纲五常观念,其深入人心,宰制人民行动的力量更是无所不入。
总之,儒学提供了帝国的价值规范,而且帝国的一切行动也都尽量在儒学中找到正当性,儒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充当帝国的守护者,一方面则排斥“异端”的干扰,在尊儒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目的,算是大部分达成了。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的诞生过程中,伴随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士大夫集团——的诞生。在这个集团中,儒学研究(尤其是经学)成为他们占有的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为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仕宦之路在形式上虽是开放的,但有能力接触儒学的,至少是小地主与商人阶级的子弟,因此士大夫成为儒学的坚强拥护者与传播者,除了部分基于对儒家理想的追求外,与士大夫集团由垄断经学而获得仕宦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此所以士大夫集团会成为坚定的儒学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对于知识阶层对文化资本的垄断,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很好的说明:
如果任何一部分文化都将成为“资本”,当这种占有受到习俗和国家的保护时,那么就一定存在着对它生产的产品的私人占有。当文化被“资本化”时,文化就变成资本,这意味着对那些拥有文化或某些形式的文化的人,把收入存了起来,而拒不把这些收入给予那些缺乏文化的人。
士大夫集团把经学研究当成文化资本加以垄断的另一表现,是经学成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懂得此一特殊文化的人才能在这个团体受到接纳,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由经学凝聚在一起的语言共同体。例如灌夫“不喜文学”(指古典学问,特别是经学),即与士大夫集团格格不入;酷吏张汤“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由于用人“依于文学之士”,得到丞相公孙弘的赞赏。对于儒学与士大夫阶级的理想与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艾蒂安·白乐日曾有一简要的观察,他说:“(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一个体系,成了士大夫背后一个组织力量,并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利益、思想和理想。……儒家学说被用作保护士大夫阶级利益的工具,其做法之巧妙(姑且不说不诚实),迄今为止欺骗了不少学者。” 士大夫集团与儒学之间的利益连系,使得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助力,更易收效。(作者:林聪舜)
林聪舜教授简介:
林聪舜,男,1953年生,汉族,台湾彰化人。曾任清华大学(台湾)中文系所主任、《清华学报》主编、傅尔布莱特奖助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的著作有:《向郭庄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10月出版)、《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史记的人物世界》(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7月出版)等。发表《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史记〉塑造的范蠡与张良的理想人生典型》、《三苏父子论刘邦、项羽》、《〈史记〉人物个别性与普遍性结合的例子——文景朝皇权与功臣、诸侯王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意义》、《激进乎?保守乎?——〈史记〉中刺客与游侠的价值观》、《叔孙通“起朝仪”的意义——刘邦卡理斯玛支配的转变》、《〈史记〉思想与先秦儒、道、法的关系》、《〈太史公自序〉中与壶遂一段对话的诠释》等多篇《史记》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