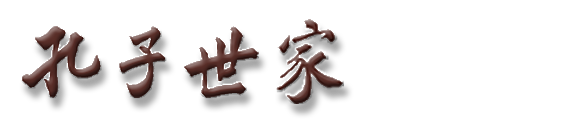心之向往,必有回应。榉溪古村一行便是如此。
9月的一个周末,应浙江嵊州孔伟东先生邀请,我们夫妇启程前往嵊州,此行目的是拜谒榉溪孔庙。
与伟东先生相识,说起来很有意思。不久前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外科学术会议,在会务组遇到卫东先生的爱女茂茂,茂茂看到我的名字,恭敬地对我说:我们是本家,我是德字辈,喊您太爷。第二天,伟东夫妇便驱车从嵊州赶到杭州,盛情邀请我们一行参加晚宴。席间,他提到榉溪孔氏家庙离他们老家嵊州不远。榉溪孔氏家庙,是我心中的圣地,十多年前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一直想去但始终未能成行。于是我们约好,择日一起游榉溪、谒家庙。
伟东先生一家四口陪同我们,从嵊州出发,上甬金高速转诸永高速约一个半小时来到榉溪村,这是个群山环抱、临水而居的古村落。
刚一下车就看到村子边白墙黑字写着《孔氏祖训箴规》,那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孔尚贤主持制定的孔氏家族第一部成文的族规。
老书记孔火春先生已经在家庙门口等候我们了。火春先生,繁字辈,年近古稀,我称他大哥,我们十几年前相识于曲阜。在榉溪,孔火春是村里不可绕过的一个人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是婺州孔氏南宗第74代嫡长孙,常年致力于孔氏家庙保护和祭孔大典的振兴等工作,是婺州南宗祭孔大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努力下,榉溪孔氏家庙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榉溪村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有一本书上这样描述他:“从未见过他大声的对人说话,从未发觉他言过其实、故弄玄虚,从未见过他毛手毛脚敷应了事,……每每见面都是小心翼翼的带有几分腼腆接人待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血脉中还流淌着圣祖‘待人以诚'的精髓。”
寒暄几句后,火春大哥便引我们去拜谒家庙。这是一处江浙地区常见的白墙黛顶叠瓦的建筑。这座建于南宋时期的家庙,说起来跟孔氏家族一段大迁徙的历史有关。
北宋的宋徽宗,是个优秀的艺术家,却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在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进攻中原,宋徽宗急忙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恒,自己带着宠臣逃到镇江避难去了。赵恒即位后改国号靖康,为宋钦宗。就在靖康元年,金兵又渡过黄河包围汴京(今开封),赵恒心中惊恐万分,急忙派人求和。金兵除了勒索大量金银以外,还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在得到满足以后撤兵北还。金兵经过6个月的休整,再次进攻汴京,11月城破,宋徽宗、钦宗被虏,废为庶人,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同年5月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位,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宋高宗同样是个无心于国、只图享乐的废物,刚一立国,就被金兵侵犯,高宗仓皇出逃,金军一路追赶,一直追到海上,未能追及。金兵在大肆掠夺以后北撤,赵构又返回临安(今杭州)。此后南宋也只偏居一隅,醉生梦死,直至灭亡。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孔氏家族有一支人“扈驾南渡”。说是“扈驾”,其实是随着皇帝仓皇南逃,在这支逃难的大军中,孔氏族人据说有100多人,大多是孔家的精英人物。其中有影响的有孔端友和孔端躬,孔端友是衍圣公,孔氏后裔的嫡传后人。孔端躬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评事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中层干部、审判长之类的职务。有的书上说孔端友和孔端躬是兄弟俩,是个误解。他们是都孔子48代孙,其44代祖是一个人,即孔勗。孔勗有五个儿子,道辅、良辅、彦辅、延济、延范,端友是道辅的重孙,端躬是彦辅的重孙。所以,端友和端躬是没出五服的兄弟。衍圣公端友这一支留在了衢州,被称为“南宗派”。端躬这一支,因为端躬的父亲孔若均在长途跋涉中患病,留在了榉溪修养,后来病逝就安葬在了榉溪,这一支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当时随着孔若钧一块到榉溪的,有他的胞弟孔若冲,以及侄辈、孙辈若干人。因为孔端躬大理寺评事的地位,加之人数较多,榉溪就自然而然成为当时孔氏家族的活动中心之一。这一支,在《孔子世家谱》上称“浙江婺州支”,也有人称之为“婺州南宗”。榉溪孔氏繁衍迅速,可谓人丁兴旺,生机勃勃,其后裔遍及四周9个县市形成了13个支派。
南宋宝佑年间,皇帝敕修榉溪孔氏家庙,按衢州孔庙例,并赐“万世师表”金匾一块,这对于婺州孔氏来说是一种难得的荣耀。现在的孔氏家庙是清代重修,坐南朝北,门口上方的匾额“孔氏家庙”四个字依稀可辨。庙东西宽21米,南北进深约40米,依次有门楼、戏台、前厅、穿堂、后堂和前院以及被穿堂分开的两个天井组成。堂间柱上刻有对联,上联是:“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育秀”,下联为:“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长流”。联中所说的尼山在山东曲阜,相传,孔子的父母去尼山祭神而生孔子,故孔子取名仲尼。而燕山则在榉溪村边。泗水在山东古鲁城北,桂水就是桂川,在榉溪穿村而过,对联巧妙的选用两地的山水之名,阐明了榉溪和阙里的渊源。
家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进得庙门便是一座戏台,戏台正对着后堂的圣人坐像,像是圣人常年端坐在那儿看戏一样。一般来说戏台是村子里的娱乐教化设施,常跟祠堂建在一块。而孔庙和戏台放在一块是不多见的,当年榉溪家庙没能申请成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因为这一点。专家们据此认为,这是一处普通的农村祠堂。后来在评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专家们认为,这是由于地处山区,土地资源宝贵,因地制宜地把戏台修在了家庙,属于当地的一个特色。戏台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字经人物备考”,下联是“一夕话今古奇观”,典型的清代对联。戏台也是雕梁画栋,有些壁画已经斑驳难认,柱梁之间的牛腿雕着精美的狮子和人物。
印象深的第二点是厅里的几排柱子,据说是84根,蔚为壮观。这些柱子支撑着这几进院落和天井,能够形成更广阔的空间供人们祭祀活动,也承载着人们对家族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印象深的第三点是,柱子的柱础,有不同的样式,从形制上看,有宋代的,有元代的,也有明清的。据史料记载,原来的家庙不在现在这个位置,清代重建时移到此处。可以想见,在当时重修时,有很多木料或者石材是从原来的庙址搬移过来的。在后堂正中孔子坐像上方,悬挂着一块匾,上书“如在”两个大字,取自《论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字迹有些斑驳,并没有上下款,不知什么年代,何人所书。
后堂之上,先祖像前,我们一行人虔诚地行了跪拜之礼。在这里,我给几位年轻人示范了怎样规规矩矩地跪拜,让他们模仿。我想,随着“跪、叩首、兴……”在庙堂中回响,孔氏家族不忘祖训、慎终追远的情怀会融入血液,一代代传承下去。
从家庙出来,火春大哥继续引我们拜谒端躬墓。端躬墓在村口,近年来重修了墓基、墓碑、护栏、香台,台阶的起端有一石像,高约1米多,一位老者挺胸站立着,双手拄着身前的一柄锄头,目光坚毅慈祥并有所思有所想。头部不知什么时候断掉过,有粘接的痕迹。火春大哥告诉我,这尊像象征着端躬祖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南下,决意弃官丢爵,扎根榉溪,做一庶民。我问这尊像立于什么时候,火春大哥并不知道,只道小时候就见有了。
墓的左前方便是那株著名的桧树王。据家谱记载,端躬南渡时,曾在曲阜孔林挖了一株桧树苗,并发誓:“此苗在何地生根,即我氏之新址也!”如今这株900年的参天大树,树干挺拔高傲,像一把巨伞擎天,庇佑着孔氏子孙后代;外皮历经千年岁月,皱褶纵横开裂,像一位农家老人沧桑的脸颊;而密密麻麻的树叶竟茁壮地像打了蜡似的,透着生机。朝向山外的方向,有两支粗壮的树干被截掉,露着断茬。火春大哥告诉我,前些年那俩枝干有些干枯了,大家都以为已经中空,锯掉后发现并没有,木质仍十分结实。专家测定,这不是桧树,而是一株罕见的红豆杉,树高37米,冠幅21米,胸围5.6米,需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实属无价的稀世古木,现已入选入选全国百棵名木、浙江省十大名树,村里人都尊其为“太公树”。站在树下,深深地呼吸,空气像是从远古而来,突然觉得异常安静,周围的山,脚下的地,眼前的桂川水,都静得那么舒适,那么恰到好处。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如沐春风、醍醐灌顶。人们说:这样的树是有灵性的。千年来,她见过太多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刀光剑影,这些故事都被她吸收进自己的根系,濡养着自己的躯干,增加了自己的胆识、阅历和勇气,也变得越来越刚正儒雅,是谓树神。
午饭后,我们继续在村子里观赏。从高处看,整个村子的形状像是一块元宝,镶嵌在群山之间。村里的路,由石子铺就,这些石子来自周围的山、溪水的底,它们或大或小,或宽或窄,恰如其分地嵌在一起,千百年来人们从上面走过,留下脚印,走的人越多,石子被磨得越光滑,也越柔和。宽窄不一的路依山而建,或平整畅快,或蜿蜒曲折,不经意的一个转弯儿,又豁然开朗,如入桃源。这些路将宋代古井、清代书院、明代古桥、十八门堂,以及不知什么年代的古庙联到一起,像珍珠缀成的苗族人的饰物那么精美,铺在大山之中。
十八门堂是不可不说的,所谓门堂,就是由主房和厢房构成的三合院或者四合院,中间有一个门堂,类似于大厅。榉溪的门堂,院落大,堂是敞开的,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抬头便是蓝天白云,初秋的阳光洒满院子,明亮又不耀眼,给人以落落大方的感受。整个布局中正典雅,装饰拙朴。走进去,并没有那种深宅大院的神秘感,其布局设置十分注重民居的实用功能。无论是晾晒的火红的辣椒,还是跑来跑去的顽童,还是门口手转着小磨的老人,都洋溢着一种烟火气,那么朴素亲切。光是看看这些门堂的名称,就知道里边有多厚的底蕴,和致堂、九思堂、仁义堂、松竹梅堂、同德堂、余庆堂……单说“九思堂”,名字取自《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氏家族是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建了多少华屋大厦,购置了多少田产,也不是有多少人当官,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色。他们继承圣祖遗风,恪守祖训,不忘初心,尊师重教,传承文脉,清白做人,勤勉读书,履仁蹈义,这才是他们的本色,也是他们的文风!在榉溪古村,九百年来,孔氏后人完整继承下来了。
有人说,在榉溪,十八门堂像一部《论语》散落在村子里。
作者:孔繁义,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沧州孔子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