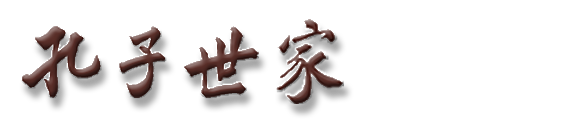文章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1日第8版
前言:
近代社会变动中的孔府
孔府在传统社会是儒脉守望者与传统士族之典范,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整合作用。清末民初,面对社会变局,一方面,孔府失去了帝制王朝的庇护,合法的经济、政治特权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孔府依然传承儒道,发挥着自己独有的影响力。这使得孔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心。近年来通过对《孔府档案》民国部分的爬梳整理,我们对这一时期孔府的权力、与国家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帝制时代,孔府被国家赋予诸多行政、司法权力,是统治着一定数量土地和人民的具体而微的政权。时至民国,政府虽名义上建立了现代司法体制,但孔府以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及曲阜周边久已成习之惯例,仍在族内、治下行使旧有“司法”之权。不过,相较于帝制时代,这类权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0年“苏景福欺孀霸产”案就是体现民国孔府“司法”实践表达的典型,值得深入探究。
案件起始:
苏张氏呈控苏景福欺孀霸产
案件始于苏张氏之夫生前与其兄苏景福分家一事。苏夫分得场园一处,但随即又租借给苏景福多年,商定“俟用时即为退还”。但苏夫死后,苏景福即生讹伯(霸)之心”。苏张氏携子讨要此地,苏景福不仅霸占不给,还将场园中“所带杨木八棵硬行卖钱”,所卖钱财据为己有。苏张氏据理力争又遭恶言群殴,无奈之下,只得于1920年2月具文向孔府呈控。
在传统社会,此类纠纷案本应由当事者诉于地方衙署。但因苏氏一族均是孔府祀田之佃户,而帝制时代孔府在此类人员所涉纠纷中确实享有司法参与权与管辖优先权,民国初建,孔府因循旧制,“司法”依旧,故苏张氏呈控于孔府并无问题。事实上,即便苏张氏将此案先报于曲阜县,也极可能被移送回孔府。例如,同一时期的泗水县佃户乔修慈控诉其兄乔修德勒价不交一案,泗水县就以“所推宅基系公府祀田……不便受理”为由,移文孔府“传案讯究”。
然而,苏张氏此呈直到4月3日方才到府。其间,此纠纷已经在刘振福等人的调处下发生新变化:苏景福不愿退地,但同意“作价二百八十吊”从苏张氏手中购买,并拟于4月13日交价。不过,随着苏张氏呈文到府,衍圣公随之批示,标志着孔府介入此案。
“型仁讲义,履中蹈和”:
孔府对苏张氏呈控的处理
孔府所批并非如苏张氏所愿,而是以双方“年齿均长”“何可以骨肉之亲,遽尔兴讼”为由,批示“着即邀同族长妥善处理此事”。此与刘振福等调处亦为一致,因此只待苏景福按时“交价”即可“永无争执”。然而,4月13日,苏景福在其子苏文善等劝诱下,“不但不交价,亦不退地”,使刘振福等“实难再处”。苏张氏遂于4月15日再上一呈,呈明最新案情的同时,亦表示“苏姓并无族长,实无人再处”“非蒙传讯究追,终伯(霸)不吐”。但孔府仍不准传讯,批复“仰该社社长、社正、村长会同理处”。岂料苏景福就是村长,且“夫子洞皆系屯田,并无社长”,苏张氏遂三上呈状。但孔府再次坚持“一宗骨肉,理宜和睦,不可兴讼”,“仍着刘振福妥为处了”。
传统社会深受儒家“无讼”思想的影响,对于民事纠纷多调处了之。孔府“远承圣泽,世守家传”,对于族内、治下之纠纷,往往在存忠恕、敦孝悌的基础上调解,故有“型仁讲义,履中蹈和”的“司法”原则。此案中,孔府一再强调“不欲使该氏伤情”,是希望涉事双方在宗族亲情中化解矛盾。而在无族长、社长调处,甚至村长就是被告的情形下,还坚持以邻里“处了”,是欲以邻里之情加以说合,均是遵循这一原则。
传府与移县:
孔府“司法”的无奈之举
刘振福等接批后,又“极力再三调处”,仍是未果,故苏张氏又于6月9日“四陈叩乞”。同日,调停者刘振福等人也上一呈,将此僵局照实呈报。如此几番呈控,加之调处无果,显然触怒了孔府,批称苏景福父子“殊属无知、荒谬已极”,同意将其传讯到府,并于7月2日发出“信票”。不过就孔府而言,此举已超出以族邻情谊来“息讼”的范畴,是族邻调处无果后的无奈之举,不应轻用。即便使用,仍然遵循“型仁讲义,履中蹈和”的“司法”原则,以孔府的巨大权威进行更高级别的调处,使涉事双方退让了事。
但作为被告的苏景福在孔府传唤之下,竟称病不到。孔府意料之外,却也无能为力,只得于7月12日将此案移送曲阜县。而移送县衙也就意味着诉诸讼狱,这与孔府一再强调的“一家骨肉,不可兴讼”无疑是相悖的。此案送至县衙后,曲阜县知事蓝晋琦“当即提讯”。据7月24日蓝晋琦给孔府咨文所称:“经多方调处,苏文祥母子愿将场园卖与苏景福为业,双方和解,愿罢讼不究”,至此案件终结。而案件移县前后不过12日,竟如此迅速解决,虽然涉事各方均为满意,但对于孔府而言实属尴尬和无奈。
空间与限度:
民国孔府“司法”的实践表达
综上,可对民国孔府“司法”实践表达的空间与限度作一总结。在空间上,民国时孔府“司法”的赋权来源即帝制王朝已经覆灭,但此案中,苏张氏却以谦卑之态,一再坚持呈文孔府,叩乞衍圣公主持公道,原因就在于苏张氏对孔府“司法”仍有莫大的信任与依赖。可见孔府“司法”的影响力在族人、佃户、庙户的心中仍存在,甚至结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依赖关系,是民国孔府“司法”实践表达的空间之一。此外,民国孔府“司法”虽无国家赋权,但旧制惯性仍为地方所承认。案件最后,曲阜县将此案终情呈报于孔府,“请衍圣公府查照并将原卷查收备案”,俨然是将孔府视为另一司法单位,为其“司法”实践表达的另一空间。
在限度上,此案中孔府的处境颇为尴尬。其本着“型仁讲义,履中蹈和”的“司法”原则,希望将此纠纷化解于亲族邻里之间,然所指派的刘振福等人一直调处无果。无奈之下,孔府只能亲自调解,而当事者苏景福竟又称病不到,真可谓“藐玩已极”。与之相对,此案移送至曲阜县后不过短短12日即告解决,且仍是“投具和解”“罢讼不究”,与孔府所欲一般无二。如此论之,孔府“司法”的实际效用已是极度衰微,发挥空间不过是基于旧日之权势,施用于依然敬畏孔府之人,对于“藐视”之徒却无可奈何。由于缺乏强制力量,孔府“型仁讲义,履中蹈和”的“司法”原则当然无法贯彻,如此孔府已很难用“息讼”调处的方式来有效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了。
作者:成积春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